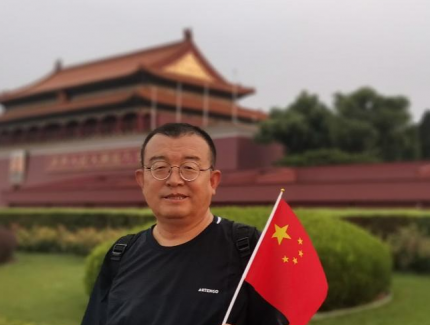在屏南,没人说得清“美”是什么,但修复古民居、开展艺术创作,还有“在地化”的乡村美育,好像最近几年县里的探索又处处和“美”相关。随着“新村民”涌入,“老村民”的生活和想法也发生变化,他们共同见证了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一个古老县域的复苏与重建。
福建省屏南县厦地村一座二层老厝,是65岁的余碧英和老伴郑德养的家。这天,二楼“闺房”里被红色系的“囍”字、拉花装点,老宅里上百年的梁柱、门窗、夯土墙似乎也放下厚重,迎来久违的喜庆。几个“森克义社”的义工把老人围了里外三层,换上大红色中式礼服,涂上眼影和口红。余碧英羞得不敢照镜子,但还是乐得合不拢嘴。
余碧英7岁时来到郑德养家,因为家里穷,没东西吃也没钱读书,所以双方父母很早就定下婚约。她感慨:“一眨眼,是土埋半截的人了,还从没拍过结婚照。”此刻,70岁的郑德养也换上新衣服,脸上“爬虫”似的褶皱被遮瑕霜厚厚盖住,他正襟危坐,双手一遍遍整理还算平整的衣角。
这场由“森克义社”公益组织策划的“夕阳厦地美”活动,是为村里的老人们免费拍结婚照。光影从天井里洒下,老厝里多了几分穿越时光的深邃感。“这种美,可能只有在800年历史的古村落里才会有吧。”义工刘晓怡忍不住说,“老房子的美感会悄无声息地浸入照片里,增加很多仪式感。”
余碧英至今也说不太清楚,村里除了风景还有什么是“美”的。但最近几年,厦地从破败与凋敝中苏醒过来,身边的种种变化又似乎处处都和“美”沾边:荒废已久的老厝恢复了棱角,“修旧如旧”的样子更加古朴、好看;邻居们拿起画笔、相机和麦克风创作,村里还涌进不少“搞艺术”的年轻人;以前无人问津的村落、山谷、稻田,竟成了“乡村美育”的实训基地。
不只是厦地,若隐若现的“美”似乎成了一条线索,串联起最近几年不一样的屏南。
古村落里的“审美”发现
为迎接这天,郑德养几天前就把老宅打扫干净,家里的花花草草拾掇了好几遍,几根腐朽的梁柱去年被换掉,屋顶的旧瓦也不漏水了。去年,老郑在庭院里新围了个花园,种上本地的“屏兰彩荷”和“屏兰娇”,宅子里增色不少。
当房门即将打开,调皮的义工刘晓怡却一把将他拦住,“此刻最想说什么?”“老婆,我爱你,希望我们白头偕老……”余碧英款款而下,郑德养忽然不知所措,在大家不断“怂恿下”才掀起红盖头,送上捧花,两人“相见”那一刻大笑起来,手挽手坐在相机前。
过去几年,厦地村——这个郑德养与余碧英托付人生的地方,像新鲜出炉的纪录片,正在显现色彩与生气。这天拍摄结束,郑德养家归于平静,厦地村也在夕阳里默不作声。启基于元,成形于明,鼎盛于清,当一个村庄见证了800年兴衰,自有一份淡定从容:夯土墙与木构楼的经典结合,依山而作的村巷和溪桥,绕水而成的耕田和茶园,窗阁廊台叠措间尽可感受历史沧桑的细节。
然而,厦地也曾和全国8155个登记在册的传统古村落一样,在某段时间陷入困顿:2015年前后,因雨水冲刷、房屋年久失修等原因,很多村民搬迁到村庄上游另造新房,加上宅基地复垦,村民外出务工,学校撤并浪潮,曾经的“屏南四大书乡”之一濒临消亡,只剩下十户人家。
 程美信到厦地村抢修的第一座老厝,曾是清代驿站,在雨水冲刷下摇摇欲坠。如今已被“修旧如旧”。
程美信到厦地村抢修的第一座老厝,曾是清代驿站,在雨水冲刷下摇摇欲坠。如今已被“修旧如旧”。
2015年10月,瑞典籍华人,被称作“中国独立文艺批评第一人”的程美信来到厦地村,投入到古村落修复工作中。几年过去,程美信的体会是厦地和周遭很多古村一起,经历了“一场审美上的觉醒”,由此展开的“活化”运动让县域发展迎来新的际遇。
埋藏在鹫峰山脉中段纵横交错的山岭褶皱里,屏南的兴衰自有宿命的味道:每逢中原战乱,衣冠士族都会避祸八闽,躲进大山里安居乐业、耕读传家,很多“单姓”村落就是见证。虽然工业时代屏南难逃人口外流、产业凋敝、老屋荒废的厄运,但仍较完整地留存的100多个汉族古村落、28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与中国传统村落,是这个古老县域的勋章。
20世纪90年代,当旅居瑞典多年的程美信回到老家安徽绩溪县,发现记忆中灰墙黛瓦、飞檐翘角、古韵丰存的“故乡”已难觅其踪,曾经古徽州代表的歙县、绩溪县变得千篇一律、毫无个性;改革开放前皖南随处可见的古村落,只剩下西递、宏村等零星几个因摄影旅游经济“幸存”。
所以当2015年与屏南初次邂逅时,“从惊喜到焦虑”的复杂情绪萦绕在程美信心头:在这里,虽然故乡的“躯壳”仍在,但古村审美价值正在消亡并伤及乡村根本。“双溪镇最有代表性的豪宅‘薛府’,主宅大面积坍塌,屋顶稀稀拉拉几张瓦片,满地杂草青苔,被当地人称作‘鬼宅’;厦地的岁进士大院在十多年前被村民们卖掉整个‘屋架’,上好的杉木也就卖几千块,现在修复则要上百万元。”
“人人都是艺术家”项目发起者林正碌也有类似感受。他通过“七天教会村民油画”的方式,在屏南漈下村开展公益美术教育。“想去村民的老厝里看看木雕,得到的答复是‘又暗又破有什么好看’,旁边另一村民凑上来,‘新厝买在城关了,现在谁还要老屋’,说完满脸的傲娇。”
长期从事艺术品贸易和公益艺术培训事业,让林正碌对20世纪90年代开始席卷乡村的“城市化运动”心存芥蒂,盲目的现代化和消费主义让瓷砖马赛克、铝合金门窗、塑料扣板等铺天盖地涌入,乡村多元化的文化个性、审美特色消磨殆尽;随着乡村审美的“失守”,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念也日渐式微。
屏南乡村振兴院执行院长潘家恩觉得,古村落的“美”不单是感官上的体验,也关乎乡土文明的延续,是每个村落独有个性之所在,村民们理应作为独立自觉的文化主体去坚守这份价值,否则就会影响公共生活的品质和活力,进而导致传统乡村价值和家园意识的双重“失守”。
2015年10月,程美信辞去大连理工大学教职,在屏南县“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支持下,组建森克义社公益组织,开始厦地村的修复和保护工作;林正碌也被县里聘请为文化创意产业项目总策划,除了开展公益艺术培训,还开始了对龙潭村、四坪村等村的修缮。
领导小组组长、时任县政协主席周芬芳明白,全县百年以上自然村有150多个,按传统“政府项目发包”的方式保护根本不现实,审美和技术上的问题更难解决。所以,她认同这些艺术家们的思路:深入古建筑肌理,提供审美上的把握,让村民更多参与到具体修复工作中去,并通过一些艺术性的实践和教育进一步激活他们的主体性,重新构建乡村的审美价值,最终实现要素回流、“活化”乡村的构想,推动精神和物质层面的乡土重建。
在修复中塑造“主体性”
这天一早,来自青海的31岁的祁国艳站在屏南县熙岭乡四坪村“22号老宅”前,她叉着腰,长舒一口气:“终于收拾好了,这可是两个月的成果!”只见“祁国艳手作IPA啤酒工作室”的木匾被挂在大门正上方,老宅共200平方米,一层经营独立品牌的“示耳”精酿啤酒,二层的三间房作为民宿。经修缮改造后,老屋整体外观仍是黄墙黛瓦,在村里毫无违和感,传统的土木结构、榫卯工艺全部保留下来,挡墙、吊顶及柜子用料都是本地上好杉木,能很好吸收水气。
“每片旧瓦我都留下来了,底下垫了防水布后重铺一遍,再也不会漏雨了!”祁国艳强调,“为增加屋内舒适性,前后两个天井还用钢化玻璃封顶,房间土墙上开了小窗,通风、采光都提升了很多,客房里还有‘独卫’,都是村里师傅们根据林正碌老师的手绘图纸做的。”
在两个月工期里,每天都有四坪村的几位工匠来干活,包括3—5位木工,一位泥水工、水电工和小工。这些工匠每天工资在150元—350元/人,再加上材料费用,修缮共耗资20万元。
一旁的木匠、四坪村村委会成员65岁的潘华亮说:“用什么木头、木梁多粗多长、风水上有什么讲究,我们最熟悉,林老师整体把握风格就行。”
2017年,六百多年历史的四坪村里绝大多数老厝处于遗弃、荒废的状态,全村一百多户籍人口只剩下十几人还在村里。村委会经房主同意后,将还有抢救价值的古屋收走进行收储、修复和租赁,租期一般是15—20年,租期结束后房子重新交还房主。祁国艳这样的承租方直接向村委会租赁。
目前,屏南普遍遵循这样一套方案:古屋租金每年每平方米3元,承租方出资修缮古屋,到期后出租方收回;村民手握产权,不掏钱还能收租金,承租方门槛低、压力小,实现双赢。
但祁国艳工作室属县里的文创项目人才引进,由政府出资;然而该项目却未经设计、预算、财审、招投标等环节,而是村里直接聘请工匠、自行采购材料,村民“投劳投工”。这显然不合规定。
领导小组成员、曾任县审计局局长的陆坚介绍:项目投资前期,各项流程就需3个月以上,并产生项目设计费、预算咨询费、招投标代理费、监理费等间接费用,约占总投资的30%至40%;且工程一旦外包就“没本地人什么事了”。
麻烦还不止于此。当2017年林正碌开始修复熙岭乡龙潭村时,他发现根本无法走招投标程序,因为这些老房的修复重建均属于“非标做法”。
“很多老屋表面上可能只破了一片瓦导致漏水,但实际上会坏掉六七片;还有檩条,下面看上去完好无损,上面却已经腐烂,到底是要三条还是五条?所以根本无法再招标前提供设计图纸。”林正碌说。
程美信解释,古村修复本就是一个“守成”的工作,市面上几乎没有合适的设计师,专业设计师多是设计新项目,对老房子理解并不深入,要么收费高昂,要么就用“套图”;再“发包”给第三方,更增加了从中克扣、以次充好等不可控因素。
于是在2017年,龙潭村干脆重拾原先“起厝”的土办法,采购多少材料、用多少工,包工包料来做,料款和工钱两者相加就是总费用。在用工、用料方面,本地工价、材料价格透明;村里还成立小型项目部,每天对进料进行管控、对用料进行结算,并通过村务监督小组审核、村账乡管等机制,防止基层腐败发生。
谈话间,潘华亮拿出手机展示他当天的“领料单”,上面明确标注采购了2块杉木板,规格是:2米×2.5米×自然厚度,58元/平方米。“每天的费用我都报给村里,村里再报给乡财政所。”潘华亮说。
但是,“土办法”最初还是存在法律和政策上的争议。恰巧时任熙岭乡乡长的张宜世是“会计”出身,县里要求他用“财会语言”提炼,于是土办法就成了“工料法”:“工”是聘请工匠和村级管理人员误工补贴费用,“料”是由村级组织自行采购的合法原材料,由此草拟《熙岭乡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建设实施细则》等一系列文件,逐级上报至县委、省住建厅和审计署广州特派办。
张宜世至今还记得住建厅一位领导在龙潭村调研时说的话:“这个办法,找外国专家设计‘鸟巢’‘水立方’肯定没戏,但修复这么多古民居,就是个好办法。”
2018年9月,“工料法”入选住建部乡村营建优秀实例,部分细节被纳入2022年中央1号文件,周芬芳、陆坚等人松了口气。程美信、林正碌也找到了一种最适合参与古村落保护的方式:作为独立第三方介入,不涉及项目资金,也不代表甲方和施工方,就是“指导”前期施工和后期活化利用。
厦地村最先修缮的是溪边两座民居,400多平方米抢修仅花了12万元,这点钱按“公建项目”走,可能还不够请一个“三流设计师”。到2018年底,厦地总计投入800万元,近60座大小宅院被修复,比传统方式节省一半以上,“关键是当地村民作为主体参与进来,修缮质量和风格美学上都有保证。”程美信说。
 溪流从龙潭村穿过,两岸的古宅多数已被新村民“认领”。
溪流从龙潭村穿过,两岸的古宅多数已被新村民“认领”。
目前,全县已累计对500多栋古民居分门别类实施抢救性修复,并成立了工匠协会,组建了5支以传统工匠为主、共100多人的古建筑修缮队伍。他们都是像潘华亮一样的本地村民。
“最近两年,有外地媳妇嫁过来了。”潘华亮说,现在他常会带着朋友参观自家祖宅,也会不厌其烦地介绍四坪村茶盐古道的历史,心里说不尽的荣耀。
找寻“生命本真”的快乐
于是,自己动手、修复古村成了村民们最初的“审美实践”。“古民居在遗产修缮复原、统筹规划后,更多的审美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就会释放出来,成为具有社区服务、文化艺术培育、村博展览等综合性服务的公共配套空间。”森克义社负责人文嘉琳说。
最近几天,在“森克社区”运营的双溪镇“第一豪宅”薛府内,总能听到复调音乐大师巴赫的“小步舞曲”;为镇上孩子们提供免费钢琴课的是四川师范大学的音乐老师王洁,她将作为义工为附近孩子们带来20节课的钢琴体验。
“琴声在杉木、松木间游走,抬头便是精美的木雕和青瓦,在这里体验中西文化交融,就是最好的教育。”王洁说。
在占地2500平方米、始建于乾隆年间的古老宅邸里教钢琴,是王洁前所未有的体验。随着2017年程美信团队对薛府进行修缮和运营,如今,这座宅邸已作为双溪社区文化艺术中心为周边村民提供免费服务。抬梁与穿斗混合式梁架结构,三进式的建筑风格,每年吸引访客3万人次。
有过“又贫又难”的经历,屏南更懂得保护与探索古村的美学价值。潘家恩说,近年来,很多艺术乡村建设并非“不美”,但却普遍存在村民参与度低、利益难以保障、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有些最后成了写生基地或旅游景点,很难与乡土社会真正融合。
但在屏城乡前汾溪村,有一群人的理想似乎还高于“融合”。2019年,位于前汾溪村的“乡野艺校”成立,发起人是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陈子劲,他和他的学生们还有一份从古村落的人文美学价值中寻找生命本真的“野心”。
3月30日晚,前汾溪村夜幕降临,一场篝火晚会让村子没有像以往一样陷入沉寂。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位乡村美育的从业者,各类画家、音乐人、艺术家相聚一堂,歌声、舞蹈、欢声笑语萦绕在田野上空。
这是“首届全国乡村儿童美育公益行动论坛”的沉浸式开幕式。白天,大家看到依山而建、傍水而栖的村子,在“三纵八横”的古巷道中感受历史的温存;晚上,篝火、草地和星空则提供了自然与人的亲密接触,让参会者自然而然地进入美育主题。
论坛承办方“乡野艺校”的负责人、1995年出生的毛华磊说:“我们更希望大家感受乡村田野带来的真挚和自由,体验发现和认知带来的美感。这也是三年来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所以在这次活动中,充满了“旧建筑叙事”“一人一故事剧场”“自然感知音乐艺术”“共生舞蹈”等千奇百怪的工作坊。
在“美育教师个体发展”环节:主持人要求大家跟随音乐寻找伙伴,分享在前汾溪发现的美。来自湖南的雅瑜老师和首都师范大学美学教育研究所的陈美峰结成对子。
雅瑜说:“我找到的是还未出现的‘美’,前汾溪小学门前种着葡萄树,已经可以想象当葡萄叶生长满枝,葡萄成熟时,孩子们在下面玩闹该有多美好。”
陈美峰说:“我发现村头溪边有两只番鸭,它们在村民家门口毫无拘束地踱来踱去,这感觉真美。”忽然她意识到,“我从小接受各种绘画课程,时常出入艺术场合,和一群陌生人共同感受人类精神的结晶,却忘了周围最朴实的美景。”
这一场景,也让毛华磊回忆起三年前村里的第一堂“乡村美育课”。
2020年1月,在陈子劲支持下,他的学生毛华磊和王润家,以及另外两名小伙伴共同创建了“乡野艺校”公益品牌。但毛华磊最初的感受是“好山好水好寂寞”。700多人的村庄,只剩下230人还在村里,仅有的小卖部里是各种“山寨”产品,老人一顿饭吃三四天……
陈子劲建议,不妨遵照“丈量、整理、想象、建设”的思路,以个人为尺丈量村庄,梳理乡土文化、历史脉络、社群记忆,与生活细节建立联系。
于是,乡村艺术课堂诞生了。从前汾溪小学的全部十几个孩子开始,艺校老师们把课堂设在校门口的菜地、错落有致的梯田、老厝里的杂货铺;上课内容也没有限制,去农田里观察昆虫;用修复老厝剩下的材料做拼贴画,和村里的长辈学习扎染技艺……
 来自上海的民谣歌手孙大肆在教屏城乡前汾溪小学的孩子们唱民谣。
来自上海的民谣歌手孙大肆在教屏城乡前汾溪小学的孩子们唱民谣。
恢复传统节庆也成了美育的一种方式。2019年初,乡野艺校决定恢复当地中断多年的“三月三上巳节”,有村民说以前“三月三”是要“舞火龙祈福”的,但已经中断了70多年。于是,毛华磊、王润家和70多位村民上山砍竹子,男人们没日没夜地打造龙框架,女人们则用稻草编织“龙鳞”……10天过去,一条崭新的百米长龙“停放在”郑氏祠堂门口,40多位村民舞起巨龙,从祠堂前一直沿着溪边舞了几百米,百余位村民共同见证……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村里‘土叔’郑振如的变化,原来沉默寡言,就喜欢坐在角落里抽烟,但为了过节,‘土叔’自告奋勇把最重要的‘龙头’做出来,村里人看他的眼神都变了。”
“我们希望通过‘乡村美育’引导村民们发现生活之美、创造生活之美、拥抱生活之美,让以前生活里被不断忽略的东西也变得有一些意义。”
新村民到访及要素回流
如今,“美”的线索还在屏南延续。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秘书长王金妹说:“县里有个‘三创三引’的思路,在这个框架里面,很多事情形成了机制:比如老屋流转,村级组织可作为中介让老屋不再闲置;还有老屋修缮,由‘新村民’出资、驻创专家设计、村委会代为建设的方式既便利租户又实现技艺传承和老屋保护;还有就是‘工料法’,提高工程效率,节约工程成本,增加农民参与度。”
“三引”则主要针对三类人,像程美信、陈子劲、林正碌这样的“高人”,对他们实行“一人一议”的支持;改善创业环境引回“亲人”,包括村落基础条件、落实创业奖补等;构建新型社区引来“新人”,根据人群分化特征,接纳新村民认租修缮房屋,来屏南定居。
32岁的江西人胡文亮来到龙潭村已有六年。“檀舍”,便是胡文亮将一所老屋修缮后的工作室。屋角的黄酒坛堆得有一人多高,“我把邻居曾伟设计的油画、动漫、四平戏等文创元素融入屏南黄曲糯米酒的包装上,年轻人喜欢喝酒,也爱收集上面的文创。”胡文亮说。
目前,全县已有200余位“新村民”来到屏南,公安部门为他们颁发《居住证》,可以和“老村民”享受同等教育、医疗等权利;同时,新村民也逐渐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去。
2021年,龙潭村迎来村级换届选举,专门设立了1个“新村民”小组,进行“新村民”选民登记,发放选民证,让他们履行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选出了三名村民代表。胡文亮提到的曾伟也是龙潭村第一批“新村民”,他当选为龙潭村第一位“新村民专职副主任”。
“通过新村民的专职专选,拓宽新村民履行民主政治权利渠道,关键是能增强他们的参与感和归属感,让新老村民更好融合在一起。”龙潭村党支部书记陈孝镇说。
六年前,曾伟在村里租下一幢10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花了几十万元改造成书屋,名为“随喜”,希望在乡村推广免费阅读。这些年来,龙潭村民干脆把“随喜书屋”当成了公共图书室,有事没事就去翻一翻。曾伟也已经习惯了村里人“曾老大”的戏称,“感觉自己真正属于这个村子了,也多了一份责任感。”目前,他更关注村里的人才引进、项目招商等工作。
如今,100余名“新村民”入住龙潭,画室、咖啡馆、小酒吧、书屋等“古宅”矗立两岸,拿着画笔的农民、直播分享的创客、古朴的四平戏唱腔混合着电子吉他声……传统与现代在群山之间碰撞交融。
放眼全县,屏南县政府与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联合成立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著名的文化IP南京先锋书店落户厦地村;复旦大学本科生教育基地建在了前洋村;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在四坪古村复垦了80多亩水田……
一切看上去都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但程美信总觉得,乡村建设不应只是保护古村,发展产业,水电路气这些,在他心里,似乎还应有梁漱溟、陶行知等人笔下,那些涉及文化启蒙等更丰富的内容。
这种不确定,就像四坪村33岁的沈明辉搞不清楚自己是“新村民”还是“老村民”一样。如今,他仍被髋关节的疼痛折磨,身高1.16米和母亲一样都是侏儒症患者,父亲是聋哑人。5年前,他在双溪镇上的菜市场里跟父亲补鞋,穿着小丑服吸引顾客。
2015年10月,屏南双溪镇国际残疾人公益教育中心成立,在林正碌老师的指导下,沈明辉开始学画之路;如今,他已经可以“以画为生”,每幅作品售价300元—3000元不等,最著名的作品《生命之树》以1.1万元价格被收藏。
“那段时间,我每天从上午8点一直画到晚上11点,是前所未有的快乐,画树林、画河溪、画古屋、画村子、画自己……拿起笔时,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也开始发现身边‘美’的东西。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在主动思考一些事情。”
“思考什么?”记者问。
“你听听我的原创歌曲吧。”想了半天,他并未直接回答。
“前方的路,你不知道有多难,往前走,不停留,不后退……”抱着尤克里里的沈明辉毫无拘束,闭上眼、仰着头,纵声高歌。
2019年底,他在四坪村认领了一座破旧老宅,经修缮后,作为油画工作室开始运营,起名为“重(zhòng)土空间”:意为尊重这片让他重生的土地。
也许这种重生才更接近程美信对乡村建设的期许吧。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韩啸